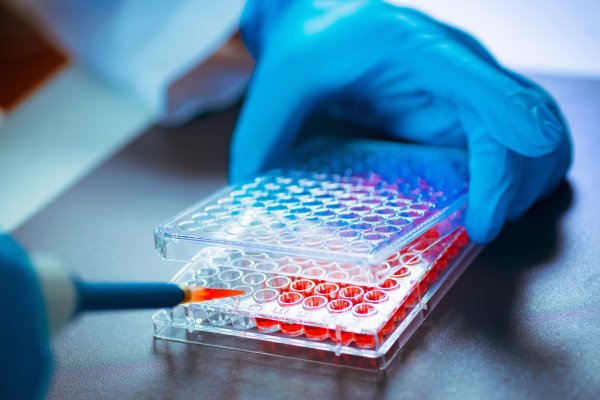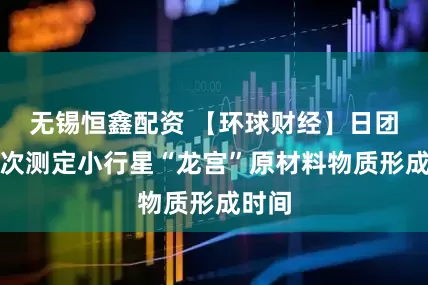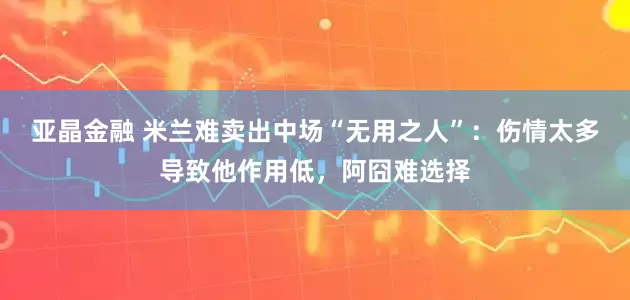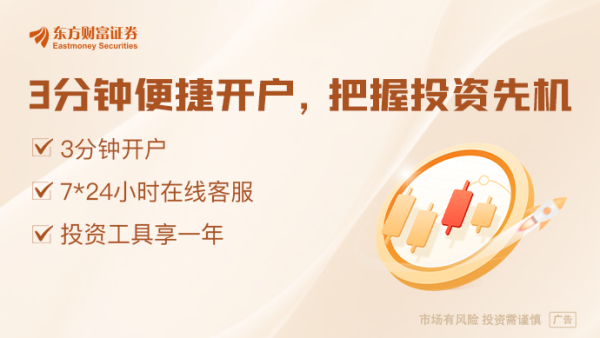孔门弟子闵子骞的祠堂在哪里?项羽美人虞姬的墓园在何方?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写于何地?大文豪苏轼为什么多次经汴河到宿州游历?今裕堂
宿州,皖北名城,乃兵家必争之地。从春秋战国到楚汉相争,宿州大地群雄逐鹿,风起云涌。宿州文化底蕴深厚,气象雄浑,人杰地灵,引得历代文人泼墨挥毫,发思古幽情。本期的安徽人文讲坛,让我们品读诗词,沉浸式感受宿州的楚汉雄风、汴水诗情。
讲席教授
甘松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,文学博士,硕士生导师,兼任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,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多项,省级科研创新团队“安徽文献与文化数字传播”负责人。独著《明代词学演进研究》、合著《唐宋词与唐宋文化》《宋元词学史》《宋元明词选研究》,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

“鞭打芦花”与闵墓松风
中国古话说“百善孝为先”。孝,小则可以修身齐家,大则可以治国安邦,使社会安定。孝文化,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讲席教授甘松在讲座中介绍,孔子有一个弟子名叫闵子骞,以孝著称今裕堂,德行与颜渊齐名。孔子感叹:“孝哉闵子骞!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(《论语》)孔子为什么称赞闵子骞的孝行呢? 有一个“鞭打芦花”的故事。闵子骞幼年丧母,冬天到了,后母给二个亲生孩子做了又厚又暖的棉衣,却为闵子骞做了一件芦花衣。芦花衣,外表蓬松但并不保暖,所以闵子骞冻得直打哆嗦。有一次父亲外出,闵子骞驾车,手冻得抓不住缰绳和马鞭。父亲见状非常生气,一把夺过鞭子向他抽去。鞭子把衣服抽破了,芦花露出来。父亲弄清缘由之后想要休妻。但闵子骞跪在地上为后母求情,说:“母在一子寒,母去三子单”。父亲这才平息怒气,取消了休妻念头。后母非常感动,改过自新,把闵子骞当亲生儿子对待,从此,一家人和和睦睦。 闵子骞的故事,后世广为流传,被收入元代的《二十四孝》,宋元时期还出现了无名氏戏剧作品《闵子骞单衣记》。
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不少吟咏闵子骞的祠堂、墓地的诗歌。明代弘治版《宿州志》,收录了明代毛简的《闵孝孤坟》写道:“人生百行孝为先,千古谁如闵子贤。茅屋只闻人语共,芦花不欠母心偏。春秋已历桑田变,乡里犹将姓字传。”明代宿州知州李化龙写有《闵子祠》:“闵子祠堂官道西,芦花满地草萋萋。阶前几棵长松树,不是慈鸟不敢栖。”闵子骞的祠堂和墓地,今坐落在宿州市埇桥区曹村镇的闵祠村。闵子祠内,现存一棵古柏,树龄约2500年,相传是闵子骞亲自栽种,所以称之为“闵柏”。古柏枝干遒劲,遮天蔽日,庄严肃穆,守护着闵子祠。闵子祠北面,是闵子骞墓,外形为大型的锥形土堆,高约10米,东西、南北各长数十米,非常壮观。墓地上,松柏苍翠,绿草萋萋,清风吹过,松枝拂动,“闵墓松风”是古代“宿州八景”之一。
历代文人凭吊虞姬墓
“霸王别姬”的故事,中国人家喻户晓。虞姬是项羽军中的歌姬,深受项羽宠爱。《史记》记载说:“有美人名虞,常幸从。项王南征北战,一直把她带在身边。 垓下之战,是楚汉相争的决战,项羽深陷重围,“四面楚歌”。项羽慷慨悲歌,唱道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?”唱了几遍,项羽和虞姬都流下了眼泪。项羽突围失败,最后自刎乌江。至于虞姬的下落,司马迁没有记载。西汉陆贾《楚汉春秋》记载说,项王唱完后,虞姬唱了一首《和项王歌》曰:“汉兵已略地,四面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!”相传,虞姬唱完,泪流如雨,拔剑自刎而死。
虞姬死后,后人把她葬在灵璧县城东,其墓地临近垓下战场遗址。虞姬墓,现在坐落在灵璧“虞姬文化园”中。虞姬墓前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,碑额上横书“巾帼千秋”,墓碑两边有石刻楹联:“虞兮奈何,自古红颜多薄命;姬耶安在,独留青冢向黄昏。”上联化用《垓下歌》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句,下联化用杜甫《咏怀古迹》“独留青冢向黄昏”句,上下对句,一问一答,情感浓烈,悲叹虞姬的不幸遭遇。
历代文人吟咏虞姬墓,发思古幽情。虞姬文化园中的碑廊中,镌有十余首佳作。例如,北宋文豪苏轼《咏虞姬墓》云:“帐下佳人拭泪痕, 门前壮士气如云。仓皇不负君王意,只有虞姬与郑君。”项羽死后,不少人改变志向,背叛项羽。刘邦命令项籍旧臣不要避“籍”的名讳,只有郑荣拒不奉命,因而被逐。苏轼在赞扬虞姬和郑荣品性坚贞的同时,也对那些不坚贞者给予批评,可谓有褒有贬,爱憎分明。南宋范成大《虞姬墓》云:“刘项家人总可怜,英雄无策庇婵娟。戚姬葬处君知否?不及虞兮有墓田。”首句“刘项家人总可怜”,是说刘邦和项羽等英雄的家人在楚汉战争中都深受苦难。“英雄无策庇婵娟”,写霸王别姬,英雄末路,虞姬不愿苟且偷生,命运悲壮。戚姬,指汉高祖刘邦的宠妾戚夫人,刘邦去世后,吕雉掌握朝政大权,对戚夫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迫害,戚夫人死得非常悲惨。戚夫人死后,没有留下墓地。同样是君王的宠姬,同样是命运悲惨,但虞姬的坚贞悲壮,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与怀念。
白居易的符离之恋
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青少年时期,寓居宿州符离二十余年,写下了大量诗篇,留下难以割舍的符离情缘。”甘松介绍道,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,其父白季庚在徐州为官,十一岁的白居易与家人迁居离徐州城不远的符离。白居易天资聪颖,刻苦攻读,十六岁就写出名篇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广为传诵。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唐代科举有“行卷”的风气,考生在考试之前,把自己平时创作的诗文送给社会名流或考官进行品评,用来提高身价,获取名声。年轻的白居易带上诗卷到长安,向前辈诗人顾况请教,顾况先看他的名字,说:“长安米贵,居之不易,居住在这里可不容易啊!”这是拿白居易的名字开个玩笑,也流露出一点轻视这个后生小子的意思。等读到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这首诗,激赏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一联,笑着说:“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在长安居住下去也就不难了啊!”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。”诗歌通过铺叙芳草,表达送别之情,又蕴含哲理,是一首野草颂,也是一曲生命的赞歌,令人回味无穷。
符离时期的白居易,除了闭门苦读,最幸福的时光很可能是在邻家女“湘灵”姑娘的温柔陪伴中度过的,两人青梅竹马,经常幽会,写下不少感人至深的爱情诗。俗话说,情人眼里出西施,《邻女》写道:“娉婷十五胜天仙,白日姮娥旱地莲。何处闲教鹦鹉语,碧纱窗下绣床前。”少女湘灵亭亭玉立、美若天仙,她的美貌能比月中嫦娥,又如旱地里的莲花,让诗人难以忘怀。离别的日子,白居易会鸿雁传书,寄托相思。《寄湘灵》:“泪眼凌寒冻不流,每经高处即回头。 遥知别后西楼上,应凭栏干独自愁。”不论相距多遥远,诗人都知道家乡西楼上,湘灵倚在栏杆上,忧愁远眺,留下孤独的身影。遗憾的是,由于双方门第有别,二人多年的苦恋遭到白居易母亲反对,有情人难成眷属。白居易考中进士后,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(804)携家人搬离符离,迁居长安。临行前诗人暗地里与湘灵道别,写下饱含热泪的《潜别离》:“不得哭,潜别离。不得语,暗相思。两心之外无人知。深笼夜锁独栖鸟,利剑春断连理枝。河水虽浊有清日,乌头虽黑有白时。唯有潜离与暗别,彼此甘心无后期。”这次分别之后,他们再也没有见面。
苏轼笔下的宿州
“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跌宕起伏,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,多次经汴河往返经宿州,与友人宴酬唱饮,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。”甘松说。
苏轼第一次写到宿州,是宋神宗熙宁十年(1077),乘船到徐州赴任,途经宿州,教授刘泾写诗相赠,苏轼次韵答之,写下《宿州次韵刘泾》。宿州古城墙上,有一座“扶疏亭”,亭中现存苏轼“墨竹”石碑,上面画有疏竹二枝,题诗云:“寄卧虚寂堂,月明浸疏竹。泠然洗我心,欲饮不可掬。”据志书记载,这幅墨竹图是东坡赠给宿州太守的。
神宗元丰七年(1084),苏轼乘船离开谪居四年多的黄州,顺流而下,转入大运河,元丰八年(1085)正月初到宿州。苏轼亲家石康伯(苏轼长子苏迈续娶石康伯之女)热情款待,苏轼在宿州欢度元宵节,写下《南乡子·宿州上元》:“千骑试春游,小雨如酥落便收。能使江东归老客,迟留,白酒无声滑泻油。飞火乱星球,浅黛横波翠欲流。不似白云乡外冷,温柔,此去淮南第一州。”上片写人们在节日里冒雨春游,有美酒可以痛饮,令人流连忘返;下片写宿州元宵夜景,火炮礼花,腾空而起,星火灿烂,令人目不暇接。虽然春寒料峭,拥有美好人情风物的宿州,成为苏轼的心头的“温柔”之乡。
大皖新闻记者 陶娜
编辑 许大鹏今裕堂
大丰收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